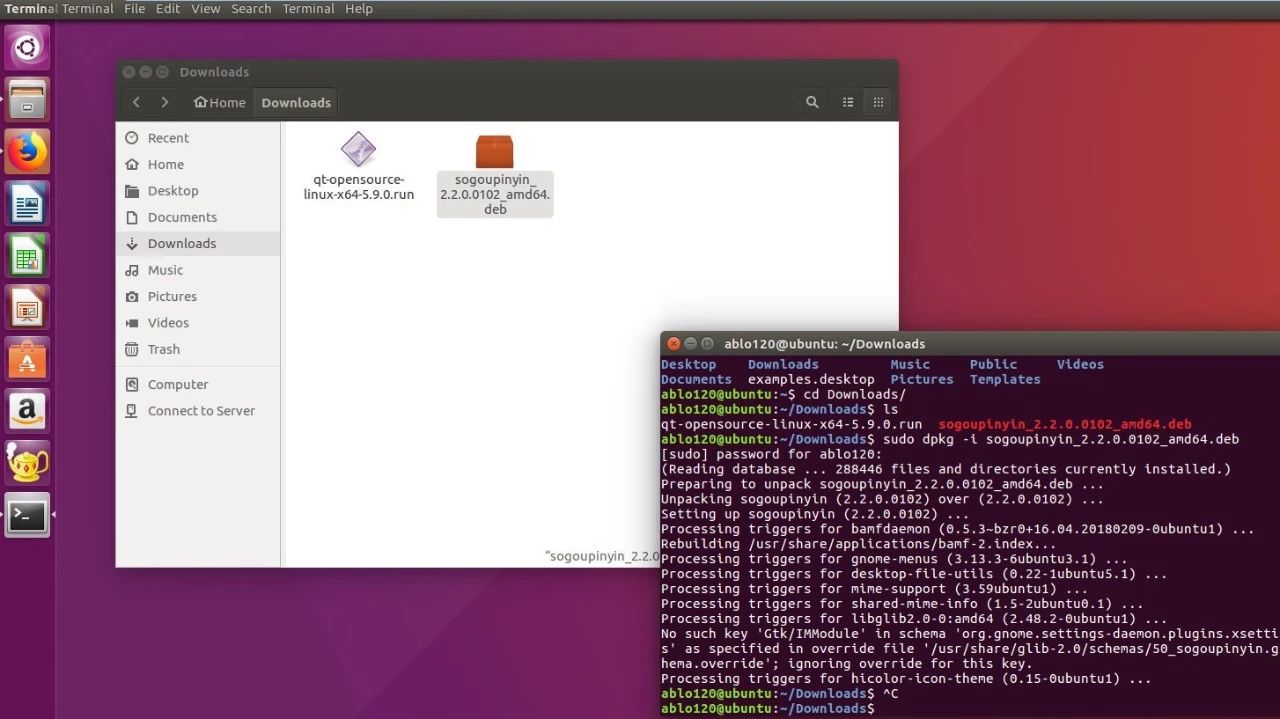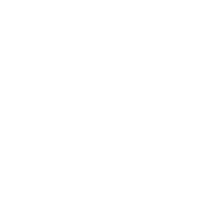实务研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种业知识产权现状与刑事保护的挑战
2025-03-04 本站作者 【 字体:大 中 小 】
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
种业知识产权现状与刑事保护的挑战
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赵政豪
摘 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种业知识产权作为促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分析了我国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种业知识产权发展和刑事保护存在的问题。一是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种业科技进步和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新品种培育有利于农业产业发展,植物新品种权是种业知识产权的核心,种业知识产权具有激励创新的作用。二是介绍了我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框架,并结合案例介绍了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等植物新品种的授权标准。三是指出我国刑事保护种业知识产权存在的挑战。虽然相关法律规定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但刑法没有设定专门罪名。实务中只能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或“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等罪名定罪。但罪名保护的法益不同,未能满足保护植物新品种权的需要。全文结合多个司法案例,论述了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种业知识产权的现状与刑事保护面临的挑战,认为应进一步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关键词:乡村振兴 种业知识产权 植物新品种 刑事保护
一、乡村振兴战略和种业知识产权
2017年10月18日,在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大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必须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指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是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主要指标。根据该规划,到2022年,作为产业兴旺重要指标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大于6亿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1.5%。事实上,2022年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了62.4%。农业科技的发展,离不开种业的进步。国家从战略层面肯定了种业科技进步对实现农业产业兴旺并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
种业是“农业芯片”,保护种业知识产权是种业科技进步的必然需求。充分发挥种业知识产权激励创新的作用,可以不断培育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的新品种。因此,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是种业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动力,新品种培育是农业产业兴旺乃至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二、种业知识产权的概念的发展
(一)种业知识产权的概念
我国法律对“种业知识产权”一词并没有直接的定义。为了探究什么是种业知识产权,或许可以先将“种业知识产权”解构为“种业”和“知识产权”两个词,即与“种子产业相关的知识产权”,再通过相关法律和司法实践了解其含义。
相关法律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种子,是指农作物和林木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条对知识产权进行罗列,其中与种业较为相关的有:“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地理标志;商业秘密;植物新品种”。
司法实践中种业知识产权相关案例也日益受到重视,2021年到2023年之间,最高人民法院每年都发布一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截至2023年共发布了35个典型案例。分析这些典型案例的案由可以发现,其中共有30个民事案例的案由是“侵犯植物新品种权”,占所有案例的85.7%。剩余的5个是刑事案例。在5个刑事案例中,有4个案例涉及销售伪劣种子,另外一个涉及假冒注册种子商标。总的来说,从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不难看出种业知识产权的现状主要是通过植物新品种权进行民事保护,通过销售伪劣产品罪和销售伪劣种子罪进行刑事保护。
(二)植物新品种——种业知识产权的核心
我国植物新品种权主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进行保护。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对“植物新品种”的定义有所区别,但是二者都提到植物新品种应当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即植物新品种的授权条件。本文通过最高法相关司法判例介绍并分析植物新品种的授权条件。
1、新颖性
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十四条,新颖性是指“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在申请日前该品种繁殖材料未被销售,或者经育种者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该品种繁殖材料未超过1年;在中国境外销售藤本植物、林木、果树和观赏树木品种繁殖材料未超过6年,销售其他植物品种繁殖材料未超过4年。”因此,如果繁殖材料相同或者申请日不符合时间规定,则该植物新品种不具备新颖性。对于繁殖材料的相同或近似,实务中需要采取检验鉴定的手段并结合相关行业标准进行判断。比如在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135号案中,最高法对繁殖材料是否相同进行判定。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检测中心出具的《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检验报告》显示,检测样品与对比品种“热抗白67”两个品种的差异位点数为0。最高法法官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玉米品种鉴定DNA指纹方法NY/T1432-2007检测及判定标准》的评判标准,认为案涉两个品种间没有差异位点,判定二者为疑同品种,检测样品构成对植物新品种权“热抗白67”侵权。同时,最高法法官认为,植物新品种是否具备新颖性,应由农业主管部门依法作出确定,民事侵权诉讼程序应当尊重行政授权程序,不应对行政机关的授权决定提出质疑、干涉或否定。
2、特异性
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十五条,“特异性指一个植物品种有一个以上性状明显区别于已知品种。”根据DUS测试标准,根据DUS测试标准,如果测试品种在质量性状上与已知近似品种有一个或更多性状存在差异,或在数量性状上有两个或更多性状与已知近似品种存在差异,或数量性状有一个性状与近似品种相差二个及二个以上代码,即可判断测试品种具有特异性。在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行终453号案中,最高法对判断新颖性的判断和特异性的时间点进行了区分,认为品种审定预备试验、通过审定初审审核等时间点,是其具备新颖性的重要事实和证据,但是与选择确定其作为特异性判断的已知品种不具有关联性。最高法认为,判断一个植物新品种的特异性时,需要确定已知的比较品种作为固定的比较对象,以考察申请新品种与比较品种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性状差异。因此,“哈育189”玉米品种不能作为判断其本身是否具有特异性的对比对象。否则,如果仅以“哈育189”这个申请新品种提出申请或通过审定的时间早于其申请品种权保护的申请日为由,就将其自身作为特异性判断的已知品种进行比较,这不符合需要多个对象进行对比检验才能判断特异性的基本逻辑,也违背了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制度的本意。
3、一致性
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十六条“一致性是指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经过繁殖,除可以预见的变异外,其相关的特征或者特性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对于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可以采取田间观察检测、基因指纹图谱检测等方法鉴定”。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1208号案中,采取了基因检测的方法。该案涉案检测报告的检测依据是:《NY2594-2016植物品种鉴定DNA分子标记法-总则》;检测所用技术手段为SSR分子标记法;检测样品为每个品种随机选取三份样品进行检测,不满足三份样品则检测全部样品,以比对每个品种样品之间DNA指纹图谱的方式验证一致性。最高法判决认为,上述检测标准和检测手段符合行业规范,通过比对送检品种“X01”和“Y01”的DNA指纹图谱发现20个位点完全一致,均符合品种一致性要求。
4、稳定性
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十七条,“稳定性,是指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经过反复繁殖后或者在特定繁殖周期结束时,其相关的特征或者特性保持不变。”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633号案中,最高法根据加盖有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杨凌)分中心的《农业植物新品种DUS测试报告》,认为测试周期符合符合NY/T2232-2012《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玉米》,而具有稳定性。
三、种业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挑战
(一)种业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体系
我国法律体系对于种业知识产权其实早有布局。《种子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假冒授权品种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生产假种子,或者生产者、销售者以不合格的种子冒充合格的种子构成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了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了假冒专利罪。可以看出,针对于侵犯植物新品种的行为,刑法并未有直接规定。通过根据最高法推出的三批经典案例来看,在实践对于侵犯种业知识产权案件的处理,更多的是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等罪定罪。
(二)司法实践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的区分及相关案例
由于种子本身就是一种产品,在实务中对销售伪劣种子的行为往往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或者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定罪,但是二罪的定罪标准和量刑标准并不相同。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条和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定罪量刑的标准是销售金额,而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对生产造成的损失。为了保证刑法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作用,在定罪的过程中如何区分两罪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刑法》规定和相关判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侵犯的客体不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保护国家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和消费者权益,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保护国家农业生产秩序和农民利益。
犯罪对象不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客体范围包括各种产品,而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仅针对种子。
构成犯罪的标准不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行为犯,以销售金额是否达到标准为既遂的标准。销售伪劣种子罪是结果犯,要求对生产造成造成较大损失。
在法院审判实务中,也对二罪做了区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新40刑终第71号案中,新疆某某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没有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销售JF606油葵种子。经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公安机关的初步核查,新疆某某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8月28日,以每公斤55元的单价,向伊宁市某某农资有限公司销售JF606油葵种子10000公斤,销售金额达到55万元。经过伊州种鉴组字(2017)3号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书证实,油葵JF606在伊犁昭苏县阿克达拉镇油葵种植区域种植时感向日葵黑茎病,为向日葵黑茎病感病品种。该病在伊犁昭苏县阿克达拉镇的爆发原因不仅是品种,也包括种植区域的气候、土壤、栽培措施等因素。最终,由于向日葵黑茎病感病的流行,阿克达拉镇种植区域种植的油葵JF606造成不同程度的减产。新疆高院认为,新疆某某行为看似符合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的构成要件。但是,结合包括鉴定意见在内的在案证据均认为造成减产的原因不仅仅是油葵种子质量,也包括气候、土壤、栽培措施因素。因此,由于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油葵种子质量这一单一因素造成的具体损失,新疆某某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行为不构成《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伪劣种子罪,但是其销售数额在5万元以上,构成《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中的薛某某销售伪劣种子、卢某某销售伪劣产品案中,二人的行为分别由销售伪劣种子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该案中,2017年3月份左右,被告人卢某某从山东、河南等地购买了大量未经国家审定的大豆种子,并将这些大豆种子包装成“农研一号”冒充合格种子进行销售。其中被告人卢某某以每桶38元的价格卖给被告人薛永贵1500余桶,以每桶36元的价格卖给周某2189桶,共计63804元。2017年3月到4月,被告人薛某某先通过卢某某购买了一批未经国家审定的大豆种子,又通过其他渠道从山东购买了大量未经国家审定的大豆种子。薛某某将上述不合格大豆种子卖给李某、郑某等多名农户,销售数额共计148480元。据河南华诚农业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检验和蒙城县农业委员会认定,卢、薛二人所销售的大豆种子均不合格。法院判决,被告人薛某某以不合格的种子冒充合格的种子销售给李某、郑某等多名农户,使购买不合格种子的农户的生产遭受较大损失,其行为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被告人卢某某以不合格的种子冒充合格的种子进行销售,销售金额达63804元,达到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定罪标准,其行为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本案因认定卢某某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证据不足,故根据刑法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卢某某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体现了司法机关严惩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司法态度。
可见,刑事审判实务中,法院对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进行了区分。由于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是结果犯,定罪量刑必须证明被告人的行为对生产造成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行为犯,只需要证明被告人的销售额。因此,当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的行为对生产造成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而销售额达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定罪标准时,可以采用该罪对被告进行定罪。
(三)实践中刑事追责存在的挑战
通过分析上述法律规定以及《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可以发现,相对于民事保护,在刑事方面我国对种业知识产权的保护仍需得到进一步加强。最高法公布的35个种业知识产权经典案例中没有任何一个对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追诉了刑事责任,究其原因则是我国《刑法》没有针对侵犯种业知识产权规定具体罪名。虽然《种子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假冒授权品种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刑法》却没有针对侵犯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规定具体罪名。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没有具体罪名就无法对被追诉者定罪量刑。导致实务中,检察机关只能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假冒注册商标罪、假冒专利罪等罪名审查起诉。
刑事司法实践仅能够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而对于种业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权利却缺乏相应的保护。首先,刑法中不同罪名保护的法益不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保护的法益是消费者的权益。而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侵犯,则是侵犯种业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权益。二者保护的法益并不相同,如果仅通过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对消费者的权益进行刑事保护,依然无法对被追诉人侵犯种业知识产权所有者权益的行为进行惩罚。其次,虽然《刑法》中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假冒专利罪等侵犯知识产权的罪名,但是这些罪名依旧无法保护种业知识产权中最重要的植物新品种权。植物新品种权归根结底是一种发明创造,假冒注册商标罪只能保护其注册的商标,无法保护发明创造过程中付出的知识和劳动。假冒专利罪虽然保护发明创造本身,但是,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动物和植物品种不授予专利权,不是《专利法》的保护对象。因此,由于中国《专利法》排除了植物品种的可专利性,植物新品种权自然也无法得到假冒专利罪的保护。
因此,虽然《种子法》第八十九条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四十条都规定了刑事责任,但是按照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仍存在挑战。根据法经济学,当侵权者的侵权成本小于侵权收益,侵权者更容易选择侵权。刑法对于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空白正是导致种业知识产权侵权频发的重要原因。随着侵犯种业知识产权行为屡禁不止,一方面会导致侵权种子大量流入市场,挤占正当品种的空间,损害农民权益;另一方面,育种者和种子企业的合法权益被侵害,创新激励被削弱,难以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最高法、最高检、农业部等部门机关也注意到了上述问题,因此近些年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大力度地推出相关的政策和指导案例。在新形势和政策的指引下,对于执法人员的种业知识产权的认识高度、种业知识产权侵权的监管和执法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结语
综上所述,文章着重分析了我国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种业知识产权发展面临的刑事保护挑战。一方面,文章强调了种业知识产权特别是植物新品种权在支持种业科技进步和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依靠新品种培育来提升农业产能和促进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文章指出我国虽有相关法律规定可以对侵犯种业知识产权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但刑法体系缺乏针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专门罪名。实务中只能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和销售伪劣种子罪来定罪,但该罪名保护的法益与植物新品种权不同,未能更针对性地保护种业知识产权。由于刑法没有有效惩治侵权的罪名,降低了侵权者的“侵权成本”,影响了种业知识产权的有效推广和激励创新的作用,制约了种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现代化进程。总体来说,文章聚焦当前我国刑事保护种业知识产权的现状和不足,认为在种业知识产权刑法体系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一方面加强种业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有利于制止侵权行为,更进一步保护种子所有权人的权益;另一方面对于监管和执法人员的认知和执法也提出了更为细致、更为专业的要求。完善种业知识产权立法、严格种业管理执法,是加强种业知识产权的保护的重要手段,是保障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合法权益的必然道路,也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目标实现的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运行绩效 ———基于品种权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任 静,宋 敏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种业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3]《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7]《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8]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135号
[9]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行终453号
[10]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1208号
[11]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633号
[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新40刑终第71号
[13]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2019)皖1622刑初141号

猜你喜欢

二手房交易流程及税费(仅供参考)


幸福的一家人作文(精选15篇)


健康生活方式的10条“金标准”!赶紧对照一下


关于潮州市光正实验学校调整学费收费标准(拟)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潮州市枫溪阳光实验小学2017年秋季一年级新生招生简章


科普添动力,实现“双碳”目标更可期


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


余额宝七日年化收益是什么意思


经前胸部胀痛,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乳腺癌?一文和你说请


汽车美容开店怎么样?